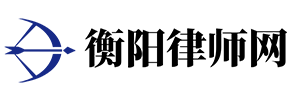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并不当然地被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与刑法第五十五条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一致。全国人大常委会1983年3月15日通过的《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二项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准予行使选举权利,他们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或者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者其他选民代为投票。由此可见,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并不当然地被剥夺政治权利,而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却无形之中给管制犯烙上了必然不能正常行使政治权利的印记。同时,刑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因此,我国刑法立法的本意应是:管制犯是否被剥夺政治权利,审判机关在判决时就已经确定,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与第五十五条相抵触。如果审判机关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罪犯在管制期间不需执行机关批准就可以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如果审判机关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则罪犯自然就不能够享有政治权利,那么执行机关应遵照判决执行,不能以批准形式使罪犯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
第二,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与宪法的基本精神不符。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参政议政和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以及对国家重大问题享有表达个人见解和意愿,而不受政府非法限制的自由,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限制与剥夺。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时,适当地限制犯罪嫌疑人的政治权利,是为了案件侦破工作的需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在管制刑刑罚的执行阶段中,现行刑法规定管制犯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必须经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执行机关(即公安机关)批准,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来决定管制犯是否享有上述政治权利,是一种变相的剥夺,这显然与宪法的基本精神不符。笔者认为,应由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来行使这项权利。审判机关对罪犯作出判决管制刑主刑的同时,由其来作出是否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既与惩罚犯罪的实践需要相适应,也与立法初衷相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三,该规定混淆了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的权限,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均可对管制犯的政治权利的行使作出决定,形成权利主体的多元化,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和完整,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不仅与法学理论相矛盾,而且导致在适用法律时混乱局面的出现。并且由执行机关来批准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标准不统一,且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程序,在同样的情况下,有的罪犯的申请被批准,有的罪犯的申请却没有被批准,影响了刑罚执行的公正性,不利于平等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种情况实质上对于管制刑的适用有极大的危害性。程序是为实体而存在,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司法公正这个法律产品非经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的运作,就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公正。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认识:对具体事件经过法定程序处理之后的结果,才是公正的。所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决定由审判机关在判决时作出,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诉讼理论,能够确保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实现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