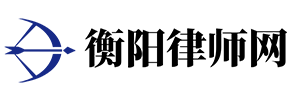最高法院的《批复》实际上是批诉讼时效期间界定为“债权人边疆不主张权利的期间”;理论上也普遍认为,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抑止债权人躺在债权上睡大觉”;审判实践中,我们的法官也是把债权人应当主张权利的时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以下统称为“上述观点”)。因此,审判实践中就顺理成章地把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债权人,其理由是,只有债权人能够证明他是否主张过权利和何时主张了权利,只有债权人才最接近有关诉讼时效方面的证据,所以,只有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才能实现客观真实。

笔者以为,“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债务人出具欠款条,债权人接受,双方当事人因该欠款条而产生两个法律后果,一是原来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二是产生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就是说,原来的债,不管是属于何种类型的债,都被新产生的债(欠款条)所代替,这在我国民法理论上称之为“债的变更”,在罗马法上称之为“债的更改”。由于债已变更,如果还以旧债计算诉讼时效,从而把出具欠款条的行为作为旧债诉讼时效中断的行为,显然是不合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如果“上述观点”将该条规定考虑进去了,那第,“上述观点”就是把旧债的消灭和新债的发生作为债权人权利被侵害的标志,或者说,“上述观点”是把债权人可以主张权利的时间起算点作为债权人权利被侵害的标志。很显然,“上述观点”忽略了债的变更这一情节,忽略了债权人的对债务人延期还款的容忍的情形,从而错误地界定了“权利被侵害”。
债务人在应当付款时出具欠款条,只能说明债务人有延期还款的意思表示,并不说明债务人不愿意还款,这样,债权人不会认为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充其量,只不能是权利实现的时间要尽、迟延罢了。何况,债务人出具欠款条,要求延期还款,而债权人接受欠款条后不提异议,应当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延期还款达成了共识,怎么能够说债权人“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呢?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债务人出具欠款条,说明债务人并不想赖帐,他并不想侵害债权人的债权,这样,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志(权利被侵害)并没有发生,所以,诉讼时效不能开始计算。只有在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时被债务人拒绝,债务人明确表示不还款或者以其行为表示其不打算还款,债权人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才能开始计算。只有这样,才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的精神。
由以上结论,我们可以说,审判实践中实行的欠款条案件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不但无法律依据,也是站不住脚的。
由于人民法院在诉讼时效问题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审判实践中,关于欠款条案件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况:债权人明明经常找债务人讨帐,就因为没有催收的书面凭据,起诉到法院后,债务人就说人家从来没找他要帐,已超了诉讼时效。我们的法官也宁肯相信债务人的信口雌黄,却不愿相信债权人信誓旦旦的“我一直在催收”的陈述,因为“债权人不能证明其一直在催收”,于是,赖帐者趾高气扬,债权人垂头丧气。法律的公正性在这里不得不被怀疑——难道这就是法律追求的目标码?其实不然。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只能为惩恶扬善而设立,都只能是正义的保护神,而不应该充当邪恶势力的保护伞。赖帐不还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它是社会稳定的大敌,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法律不期望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没有正确适用法律的缘故。
“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制度告诉我们,除少数几种依法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以外,举证责任应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来承担。在涉及诉讼时效的案件中,并于诉讼时效的问题都是债务人提出来的,那么,是否存在诉讼时效问题,理所当然应由提出主张的债务人来承担,而不应该违法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让没有提出主张的债权人来承担举证责任。债务人在证明诉讼时效已经超过的主张时,不应当证明债权人在一定的期限内没有主张权利,而应当举证证明他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之前明确表示不还款,或者以其行为表示不打算还款,亦即,债务人应当证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且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如果债务人不能证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债务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从而承担对其不利的裁判后果。如果债务人能够证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则债权人应当承担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发生情形匠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