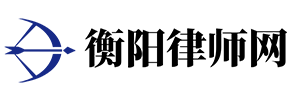目前,我国的受贿犯罪十分猖獗,大案、要案、窝案、串案层出不穷,犯罪手段不断翻新,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愈来愈大,究其原由,根本在于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中,体制不键全,社会控制力下降、市场经济的负效应以及公共权力机能示弱等因素为受贿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发育的温床。如今,受贿犯罪已发展成为社会公害,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不有效加以遏制,必将影响党群关系,影响党的形象及政府的威信,甚至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后果可谓不堪设想。在现行刑法中,我国确实对这一“顽症”痛下“猛药”,其法定最高刑更是直极刑,并处没收财产,对犯罪分子的生命与财产进行“双剥脱”,以图腐败分子能放弃犯罪念头。然而,由于现行立法未能将这一良好的立法本意完全渗透到刑法分则中,如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诸多纰漏,未能概全现实反受贿罪斗争中的复杂情势,从而导致了司法认定上的困难,以致于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加之其他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目前的反受贿斗争遇到诸多不必要的困难。为完善我国反受贿罪的立法与体制,笔者欲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拙见。

一、完善受贿立法,严密刑事法网
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分直接受贿罪和间接受贿罪两种形式。直接受贿罪系《刑法》第385条第一款的规定,也是对受贿犯罪的一般规定,其内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是受贿罪。”间接受贿行为则在《刑法》第388条中予以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从法条内容上看,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的立法与79刑法相比,并无新意。确定的受贿行为特征未能有效应对已经变化的客观复杂情势,疏漏较多。为严密法网,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对法条作出修正。
(一)受贿主体。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利用现职的职务便利索贿或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主体认定的困难。因为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与他收受贿赂的行为并不一定统一于“现职”这一时空,如在职时为他人谋利益,离职后再收取财物,或者在赴任新职前收取财物,就任新职后为他人谋利益,甚至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在任职期间分文不收,在退休后才收取或索取贿物,这些情况导致了所任职务与收取贿赂两者间的脱节,主体难以界定,证据不易把握,不利于打击犯罪分子。同时,将犯罪主体单纯地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也让有些犯罪分子有机可循。在实践中,贿赂大都由家属收取、保管,家属这种行为在受贿立法中若不有所体现,许多犯罪分子便可将其受贿行为推给家属,而自己佯装不知,从而逃脱法律的惩处。虽然新近的司法解释对此显示了关注,但与实际形势的要求还存在相当的差距。
(二)立法用语。现行刑法在界定受贿罪时所用词汇极不科学,易让人在理解时产生偏离立法原意的理解。
1、“利用”的主观性。利者,利益;用者,使用。利用,即是为了利益而使用。“利用”充分包含了施动者强烈的主观性、主动性、趋利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充分体现了施动者的主观企图。受贿罪的本质在于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制度的侵犯,其判定标准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收取了贿赂,而不在于其是否有利用职务便利谋利的企图。事实上,许多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并没有利用职务谋利的企图,甚至就是按照规距办事,却获得当事人的“报酬”。依“利用”之含义,这类情况便不应定为受贿罪,但它却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及成立标准。
2、“便利”的抽象性。“便利”,按常义理解,即某种职业、行为、事项等生成的附属性利益。这一附属性利益是基于它事物衍生出来的,并非它事物本身的内容,如巡逻中的交警有开公车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的便利,而自己去的地方未必是工作的需要,即不一定是工作的内容。所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不应包括国家工作人员正常履行职务的行为,而应仅指基于一定职务而派生出来的机会。这便造成了事实上界定哪些行为属于正常职务行为哪些行为属于职务派生出来的机会行为的困难?正如我们无法断定公路上奔驰的交警巡逻车是交警在巡逻还是交警在用公车办私事一样。况且,职务是职权与职责的统一体,两者相互依存而存在,我们该怎样确定两者间何为便利呢?如果职权是便利,那么职责是不是就是不便利呢?但因为职责事由而犯受贿罪的也不是不存在的。加之,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一定职务的实际权力要大于法定权力,实际权力与法定权力之间的差额,是否属于“便利”?这些都因过于抽象而难以认定,有待于立法者进一步讨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