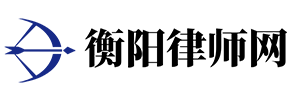出嫁女法定继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一、分离: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
(一)案例带跟我们的启示
案例:罗某生前育有长子甲、长女乙、次女丙、次子丁四个子女。甲在城里居住,乙和丙早已出嫁。生前,因病瘫痪在床的罗某随丁共同生活。瘫痪在床期间,甲、乙和丙偶尔前来探望。2011年,罗某因病去世,遗体由甲和丁共同安葬。罗某生前在银行有存款7万余元,丙起诉要求依法继承。在诉讼过程中,甲表示由法庭依法处理;乙主动要求将应继承份额赠与丁,自己放弃继承权。
丙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其依法享有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其在逢年过节时对罗某进行探望,罗某生病住院期间也前来探视,因此履行了应尽的赡养义务,应当享有罗某遗产的继承权。丁独占了罗某的生前财产且拒绝协商,因此提起诉讼。
丁认为:虽然法律规定丙享有继承权,但在罗某生前,丙没有尽到应尽的赡养义务,逢年过节的拜望走访和生病住院期间的偶尔探视只是礼尚往来的礼节,不能认定为尽到赡养义务。比如,丙对其干爹干妈在逢年过节和生病住院期间也进行走访探视,但不能说明丙对其干爹干妈尽到了赡养义务。因此,罗某的生前遗产,根据法律丙应当不分。同时,罗某生前主要是其妻子戊在具体照顾赡养,因为孝心的原因,罗某生前口头遗嘱就明确表示其死后的银行存款归丁和戊继成。此外,从来没有听说过嫁出去的姑娘回家分财产的,父母已经给予了丙相应的嫁妆,丙的行为简直是想钱想疯了,大逆不道,他们家没有丙这种人。综上所述,不同意丙的诉讼请求。
在讲求“礼尚往来”和“孝道”的中国,亲朋好友之间在逢年过节期间带上礼物到对方家中“住上几宿,吃上几顿”的习俗非常普遍,父母长辈生病住院期间前往看护或是根据家境赠与一定数额的金钱也必不可少。因此,从案例中丙丁的答辩过程来看:丙陈述的侧重点在于合法性,即法律赋予了其依法享有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至于合理性而言,其在逢年过节和生病住院期间的对罗某的探望则显得十分薄弱。丁的答辩则紧紧围绕着合理性进行,丁首先承认了法律赋予丙的遗产继承资格,随后围绕着继承份额展开反攻,包括了赡养义务、遗嘱、习俗、嫁妆和道德五个方面。从双方陈述和答辩的你来我往之间,我们看到了出嫁女行使法定继承权的尴尬:合法性十足而合理性匮乏。
(二)审判管理的数据回应
2012年~2013年,C市某基层法院共计审结法定继承案件592件,其中,判决13件,调解579件,调解率为97.80%。这些调解案件存在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有父母参与情况下,子女均放弃遗产继承权;在只有平辈亲属参与的情况下,出嫁女选择放弃继承,遗产归随父母生活的一方。
数据信息告诉我们,在法定继承案件中,诉讼主体均知道其依法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但不随父母生活的出嫁女都主动选择放弃应继承份额。当然,这并不算说出嫁女家庭富有或者不看重财产的继承或者兄弟姐妹之间感情有多深或者道德高尚而彼此谦让,而正是案例中丁的答辩理由引导着她们作出的理性选择,是一种不违反法律甚至是法律规避。
二、根源:制定法与习惯法的偏差
上文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法定继承领域的矛盾问题,即出嫁女继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分离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以一元化的制定法看待问题,而是采取习惯法和制定法的多元立场进行思考,那么不难发现,矛盾的根源正是源于现有《继承法》与习惯法的偏差。即出嫁女继承父母遗产合法但不合理,继承公婆遗产合理但不合法。
(一)身份定位的偏差
在传统仪式婚礼中,出嫁女出嫁设有辞别祖宗的仪式,婚礼之后女儿就不再是娘家人,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同样,在婆家的迎亲仪式中,也有接纳儿媳入门的仪式,谓之“嫁入我家门,便是我家人”。在嫁娶仪式中,出嫁女的身份得到了变换。这种变换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女儿不是娘家的传后人;二是婆家人对儿媳改嫁的强烈阻挠。需要说明的是,当前的婚嫁仪式花样百出,似乎已不符合本文所述内容。但在民族文化心里并没有变化的前提下,只能说是当下的婚嫁仪式与民族文化发生了脱节,没有反映出民族文化的要求,而不能以此否认出嫁女被定位为“婆家人”的传统习俗。
纵观我国《继承法》,有关出嫁女享有公婆遗产继承权的只有《继承法》第十二条:“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从法律条文的规定看,儿媳享有对公婆遗产的继承资格有两个条件:一是丧偶;二是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从悲惨的前提条件和所尽义务的苛刻规定不难看出,该条文表面上看是对丧偶儿媳继承权的规定,实际上却是为了确保老年人无人赡养的情况下对儿媳赡养公婆的提倡,用一句时髦的语言来说,出嫁女不过是“公婆”走投无路情况下的“备胎”。出嫁女在婆家的继承资格只有在被需要时方才被想起的情况,以此为据认为《继承法》承认了姻亲的法定继承权难以令人信服。与此同时,在父母遗产的继承上,出嫁女却和兄弟一样无差别地时刻被提及。现有《继承法》对于出嫁女与兄弟同等地对父母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而对出嫁女与丈夫之于公婆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字不提,反映了制定法在出嫁女继承权上始终以自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态度,并在规范上确认了出嫁女终生的“娘家人”身份。
习惯法的“婆家人”身份定位和制定法的“娘家人”身份定位的差异,造成了出嫁女在法定继承中始终属于“外人”的身份尴尬。习惯法上,“闺女哪来的继承权?再说,要是当父母的把家产给闺女,自己心里也不舒服,总感觉是把自己家的产业给了外人了。”《继承法》中,出嫁女直接被排除在公婆遗产继承的诉讼主体之外。
(二)权利义务的偏差
我们梳理出嫁女的人生轨迹发现:出嫁女总体上在娘家只享有权利而未履行义务。出嫁女在出嫁前,长时间是需要娘家人抚养、照顾、教育的对象,即使是晚婚出嫁女也不过有几年独立生活的经历而已。在出嫁时,娘家人根据习俗还要为其准备一份嫁妆,并且在讲究门当户对、讲排场风光的婚嫁文化中,嫁妆的价值不菲(相对于家庭财富)。在出嫁后,出嫁女除了逢年过节时购买礼物探望娘家父母之外(在礼尚往来的文化中,是需要比照回礼的),其不再对生父母履行其他义务。而对于婆家来讲,出嫁女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的价值,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用作赡养公婆之用,甚至在公婆的生活起居上也进行相应的照顾,对公婆尽到儿媳的赡养义务。尽管有人会以婆媳关系向来不好提出质疑,但那只不过是感情上的不和,并不能否认出嫁女在事实上与公婆有着赡养关系。纵观出嫁女的人生轨迹,可以说,其在娘家主要是享受权利而在婆家则主要是尽义务。
对现有《继承法》的检视发现,儿媳对公婆尽到的赡养义务不如丈夫享受权利后应尽的义务,也不如公婆之女不履行义务只享受权利,我们将之归纳为《继承法》中的“媳不如子”和“媳不如女”现象。
在传统习俗中,年轻人是讲究成家立业的,年轻一代成家之后,方被赋予养家糊口的职责。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下,对于负担的家庭责任来讲,儿媳和儿子所尽的义务完全是同等的,赡养公婆的义务亦是如此。但是,同等家庭责任的履行却换来了不一样的结果,丈夫毫无疑问地当然获得了公婆的遗产继承权,而儿媳在好处面前却是“靠边站”。同等履行义务而不同等享有权利,反映出现有《继承法》在男女平等上对“子、媳”平等的忽视,从而造成了法定继承规范中“儿媳不如儿子”的厚此薄彼。
《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的子女包括生子女、继子女和养子女。其中,养子女享有继承权的主要原因在于形成了法律拟制的血亲关系,继子女享有继承权的关键在于形成了扶养关系。纵观出嫁女的人生,其与公婆大抵也形成了扶养关系以及姻亲关系。如果我们将传统习俗的合理成分考虑进来,出嫁女与公婆之间的姻亲关系也可以解读为习俗拟制的血亲关系。将继子女、养子女和出嫁女与公婆的身份关系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出嫁女在身份关系上丝毫不输于养子女、继子女,并且在权利义务履行上优于养子女、继子女。而现有《继承法》对于养子女、继子女的继承权保护明显优先于出嫁女。这反映出现有《继承法》中的“媳不如女”的现象。
习惯法中出嫁女对公婆履行赡养义务的事实和现有《继承法》对儿媳对公婆履行的赡养义务的忽视,引起出嫁女在法定继承中权利与义务的分离,权利与义务的不匹配带来了出嫁女继承父母遗产“合法但不合理”,继承公婆财产“合理但不合法”的权利义务尴尬。即使出嫁女鼓足勇气要求继承父母遗产,也必然带来勇气有余而底气不足的无奈,并且造成兄弟及亲属对出嫁女的反感排斥,从而在自然血亲中“众叛亲离”。“俺要是光琢磨老人撇下的旧房,不让人笑话呀!养这种闺女有嘛(什么)用?”
(三)继承模式的偏差
在习惯法里,我们似乎看不到明显的法定继承现象,尤其是在出嫁女继承父母遗产上,但如果我们将父母子女财产的变化放置于整个人生的轨迹中,不难发现,我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子女法定继承制度。
我们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自然血亲父母对子女的关照可以归纳为两件事:一件事是对子女的抚育;另一件事是为子女谈婚论嫁操劳。对子女的抚育与传统的继承习惯关系不大,在此不作讨论,谈婚论嫁却显现出我国特有的继承模式。谈婚论嫁中,父母为儿子所做的是修房建屋,为女儿所做的则是购置嫁妆。这种习俗至今仍然流行,现在网络上吐槽的丈母娘要求女婿购买房屋就是这种习俗的延续。父母为儿子修建房屋和为女儿购置嫁妆并完成嫁娶仪式后,因父母年龄较大和对子女的责任完成,大多数就选择等着安享晚年,积极创造财富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所以,在我国的社区中父母为子女操办完婚礼后叫“上岸”。当我们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不难发现父母所有的财产在子女婚嫁之时就已基本处分完毕。这种难以现有《继承法》观念衡量的财产处分方式,笔者认为就是中国传统的法定继承模式。有人在对农村家庭财产继承进行研究后也将我国传统的婚嫁分家情况视作家庭财产的继承方式。
上面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传统的继承模式的以下特点:一是没有统一的财产继承现象,但这并不排除父母对整个遗产的统筹考虑;二是子女对父母的财产继承发生在子女婚嫁成家立业之时;三是父母的财产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没有一个确定的遗产继承数额;四是子女婚嫁完毕基本就是父母财产继承完毕。值得一提的是,儿子继承的财产主要为不动产房屋,而女儿继承的嫁妆主要表现为动产。从表面上看,这种财产的继承体现出男女不平等现象,但我们联系“养儿防老”的传统,结合儿女在父母年老时所尽义务的差异,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会是一幅儿女的法定继承权利义务合理配置的清晰图景。这种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展现了传统继承追求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和实质公平特征。
现有《继承法》的继承模式也追求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和继承权的男女平等,但现有继承法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和继承权男女平等是抽象的、理论性的,而非传统继承的实践性和实质性权利义务相一致和继承权男女平等。在继承开始时间上,现有《继承法》以被继承人死亡作为法定继承开始的时间节点;在被继承财产上,被继承财产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得到固定。这种继承开始和继承财产固定的时间点把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明确区分开来,并以遗嘱继承严格的程序和书面要求做了更加明显的划分,从而排除了父母根据子女的家庭状况分配遗产的可能,把借助父母威信实现继承人之间的互助互让转移到了法律的倡导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之下。
在传统的继承模式中,法定继承统一的继承时间和固定的财产,各自继承人继承财产的时间主要以婚嫁时间确定而不是以被继承人死亡确定,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由被继承人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自由决定。因此,两者相比起来,传统的继承模式是一种动态的,而法定的继承模式是静态的。
当社会生活习惯未发生巨变时,以静态的继承模式取代传统的继承模式会导致出嫁女参与“二次继承”现象,从而侵害到出嫁女之兄弟的财产继承权。原因在于:父母为出嫁女准备的嫁妆为动产,使用寿命较短,等到父母去世时差不多消耗殆尽。同时,由于婚居习俗的差异,女方出嫁后以随婆家居住为主,父母准备的嫁妆很容易被解释为现代法律制度中的赠与,从而嫁妆轻松跳出了遗产的范畴。但是,父母为兄弟婚嫁所置备的是不动产房屋,使用寿命较长,往往能延续到父母去世之后。在父母随男子居住的习俗里,父母与男子的财产在客观上往往混同不清。因此,无论父母是否存在赠与的意图,现代法律观念都很难为父母为男子修造的房屋的归属做出赠与的解释,不得不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再次纳入法定继承范围。这样,出嫁女如在父母去世后依据《继承法》行使继承权,不仅获得了嫁妆收益,还参与到了兄弟财产的分配之中,事实上造成了对兄弟财产权的侵犯。
父母生前根据自身意愿对自己财产的处理,因为财产样态的差异和所有权归属是否清晰,依据现有《继承法》则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这说明现有法律制度超出了当事人的意愿,这与民事领域意思自治的观念大相径庭。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出嫁女对父母的遗产选择放弃继承而对公婆遗产的继承暗中使劲,其实并非法制观念的淡薄和男女不平等的封建思想。相反,这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理性选择。
三、会通:出嫁女法定继承权的完善
法定继承中出嫁女的“有权不要”和“无权却争”的异象源自于习惯法和制定法之间的冲突,本质是制定法中的一些法律观念和法治的理念在中国尤其是在司法和社会管理实践中出现了水土不服。正如马克思曾说的:“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因此,实现出嫁女法定继承权的合理配置,需要实现以习惯法为代表的社会和以规范为代表的制定法之间的会通。
(一)完善继承父母财产规定
1.保留出嫁女继承父母财产的资格
出嫁女享有对父母财产的继承资格,这不仅是继承权男女平等中“儿、女”平等的应有内容,也是社会的一种古老习俗。同时,独生子女政策的存在,保留出嫁女的继承资格可以避免无主财产的产生。此外,在出嫁女对父母尽了赡养义务的前提下,资格的保留也为实质公平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因此,出嫁女对父母财产的继承资格是必须保留的。
2.继承份额应根据履行义务情况确定
出嫁女在个案中的继承份额,应当根据出嫁女对父母所尽赡养义务情况确定,并且出嫁女在此过程中负有举证责任。此外,出嫁女所尽义务不能以存在逢年过节的探视、病时探望照顾进行认定,而应当考虑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等综合参考。
3.经传票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应继承份额
出嫁女在诉讼过程中经依法追加并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的,视为自愿放弃应继承份额。基于婚居制度导致出嫁女对父母所尽赡养义务不一和财产管理成本偏高的考虑,出嫁女经传唤拒不到庭的,不能保留应继承份额,这是出嫁女与其兄弟在未到庭情况下的区别处理。
4.嫁妆作为遗产分配中的参考因素
出嫁女的嫁妆容易遁入父母遗产之外,因此,应当将嫁妆作为父母遗产分配的考量因素,理由在继承模式错位中已有论述。
(二)有条件地赋予对公婆财产的继承权
1.设立最低年限
法定继承虽然解决的是财产的归属,但法定继承的“财产继承人只能是与被继承人有一定亲属身份关系的自然人”。因此,身份关系是法定继承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尤其是继承人身份的稳定必须予以考虑,否则容易造成家庭财产外流弊端。
新中国成立后,在婚姻家庭领域,出嫁女获得了婚姻自主权,这与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七出三不去”相去甚远。婚姻自主权带来的是家庭对出嫁女的人身控制力削减甚至消失。对于娘家人来讲,人身控制力的强弱并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自然血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对于婆家人来讲,人身控制力的强弱则有不一样的意义,婚姻关系的不稳定导致了儿媳随时不是自己人的可能性选项。因此,设定最低年限有利于保证婆家财产“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防止一些居心不良之人借婚姻赚取财物,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伦理道德。
婚礼只是形式上实现了“娘家人”到“婆家人”身份的变换,实质上的“婆家人”身份需要双方感情的养成和彼此身份的认同,而感情和身份认同的实现都需要时间来确定。在此,笔者建议参照一些国家认定继父母子女关系5-10年不等的时间限制,原因在“儿媳与公婆关系与继父母子女关系大致等同”处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同时,鉴于婚姻关系存在所谓的“七年之痒”之说,也就是说,超过七年之后,婚姻关系也因经受了考验而趋于稳定。
综上,笔者建议将出嫁女取得公婆遗产继承权的最低年限设定为7年。
2.履行赡养义务
权利与义务一致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我国继承法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允许任何公民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因此,出嫁女享有公婆遗产继承权,必须以履行对公婆的赡养义务为前提,也是出嫁女享有公婆遗产继承权的基础。
实际上,出嫁女与公婆的关系和继父母子女关系具有大致等同的特征:一方面都是以姻亲关系为纽带;另一方面都需要彼此的扶养来实现感情的培养和身份的认同。笔者认为,现有《继承法》将享有继承权的继子女设定为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是非常合理的。既然享有继承权的继子女必须为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那么儿媳也必须与公婆形成扶养关系方能享有权利。
3.按年限分段设定比例
在习俗传统中,婚姻年限往往等同于对公婆的赡养年限,出嫁女的“婆家人”身份也是随着婚姻年限的不断增长而逐步被认可的。因此,婚姻年限可以将“身份认同”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很好的结合起来。此外,为确保身份关系与权利义务关系之间的均衡,婚姻年限不能作为单一考量元素,还需要考虑人类的生老病死规律,特别是要注重参考人类的平均寿命,因此,设定对公婆的赡养年限上限非常有必要。根据目前的晚婚晚育政策和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为75岁的实际,假如甲在25岁成婚,一年后生育小孩,及其下一代25岁时婚嫁时,甲已是51岁,距离平均寿命还有24年。因为是平均寿命,所以笔者认为,儿媳对公婆的赡养年限达到或者超过25年的,应当与公婆之子享有同等继承份额。
4.具体操作程序
第一、确定公婆之子的继承份额为单位1。无论习惯法还是制定法,公婆之子对公婆都被课以最重的毫无选择的义务,并有《刑法》加以规制,而儿媳则是有选择权的。因此,在确定继承份额上,必须以公婆之子为标准去衡量和确定他人的应继承份额。
第二、尽赡养义务不满7年的,不享有继承资格。
第三、尽赡养义务达到7年的,享有相当于公婆之子应继承份额的10%。经过“七年之痒”后,排除了借婚姻赚取财物的可能,出嫁女也就真正取得了婆家的“入场券”。之所以定为10%,主要是考虑出嫁女婆家身份的认同感不高以及公婆需要赡养的程度还不高。
第四、超过7年之后的部分,每增加一年应继承份额增加5%,达到或者超过25年的,与公婆之子享有同等同比例的继承权。之所以设定为5%,主要是实现最低年限、最高年限和“肥水不留外人田”传统的衔接。25年后,公婆均已成行将就木之人,“银婚”的离婚几率也大大减小,“财产流入外人田”的可能也基本不存在。
下面我们举一案例做示范:
例如:一出嫁女赡养公婆的年限为10年,其公婆有3个儿子,女儿未尽赡养义务不应当得遗产份额。这种情况下,我们设定公婆遗产数量为X,则出嫁女享有的遗产继承份额为出嫁女的法定继承权的设置不是一句“继承权男女平等”的口号和赋予出嫁女与兄弟平等的法定继承权就可以实现的。我国传统文化习俗对于婚姻家庭生活的安排无论如何都是法定继承制度无法绕开的。正如苏力教授所说:“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的制度。否则,正式的法律就会被规避、无效,而且会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法定继承权的平等不是理论的、抽象的平等,而是实践的实质的平等。制定法忽视社会生活习俗中的身份、权利义务,把出嫁女的“女儿”和“儿媳”身份简化为单一的自然血亲关系,必然造成出嫁女在继承中“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断裂,从而造成出嫁女在父母遗产继承上的弃权和在公婆遗产继承上的暗斗。只有将出嫁女的“女儿”身份与“儿媳”身份统一起来,设定科学的年限和继承比例制度,制定法才会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才会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所谓“法律是人们群体生活中的产物,也是在群体生活中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