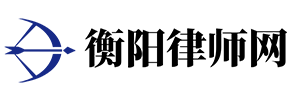我国在1979年和1997年近20年的时空跨度中颁布了两部刑法典,其中79刑法作出了有限防卫的规定,97刑法则规定有限防卫和无限防卫两种权利并存,孰优孰劣,学界和实务界都已作了热烈讨论。但至今为止,这种讨论,尚很少涉及立法主旨-罪与非罪的视角把握上,即判断某防卫行为是“正当”还是“过当”所赖于支撑的依据问题。这无疑是研究上的缺陷。两部刑法典的有关正当防卫制度规定都存在相对不完善的弊端。79刑法第十七条采用“二款”表述的立法模式只规定了有限防卫权,未免“过于抽象,不易操作,理解上的随意性也较大”,以致造成部分公民行使了正当防卫权利而被错究的情况;而97刑法第二十条则采用了“三款”表述的方法规定了有限防卫和无限防卫两种权利并存,虽可避免了79刑法的上述弊端,但却难于克服正当防卫权利往往被滥用、导致不法侵害人基本人权难于保障、动摇“罪刑法定”原则实行的新弊端。为什么存在两个“弊端”呢?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是:(一)立法信息的局限性。立法者总要受到时空条件的信息局限,无法对过去已发生的事情都能知晓,也无法对现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穷尽地掌握,更无法对未来预测,对所有的发展状况先觉先知。因此,立法上的相对不完善是在所难免的。我国79刑法是根据当时中国刚刚经历“文革”后的治安问题作出的有限防卫规定,实施若干年后,又发现新的问题:治安没有根本好转,好人怕坏人现象还存在,不少公民怕行使正当防卫权利被错究,“该出手时不出手”,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人极少;因而严重的刑事犯罪愈加猖獗,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十分不利。这种“新问题”引起了立法者对有限防卫制度的反思,着手研究新的立法,将无限防卫的设置明确规定在97刑法中,旨在加大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二)法律表征的局限性。“法律是以语言作为载体的行为规范,而语言仍是无限客体世界之上的有限的符号世界。由于语词的有限性,常常不得不使诸多客体由一个词语来表征,这就使语言具有极大的歧义性。此外,对于许多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精细的客体运动过程,语言只能保持沉默。在许多情况下,立法者只得求助于模糊语言的手段来表达只可意会的立法意图,这便造成了法律的模糊性。”法律的模糊性给法律本身造成的局限,使人们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往往相去甚远,79刑法施行期间为什么出现一些公民行使正当防卫权利被错究的情况,原因就在这里。立法上“顾此失彼”的难度,决定了司法运作仅仅从法条到法条理解立法意图是不够的。当我们站在“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超时空回眸79刑法的有限防卫和审视97刑法的无限防卫时,我们就会发现:两部刑法从有限防卫到无限防卫的立法演进,并非给实践划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提供现成的答案。因而界定某一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时,应以事实分析和法条入套为基础,以“立法”主旨为罪与非罪的视角把握,才能杜绝有悖刑法价值的错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