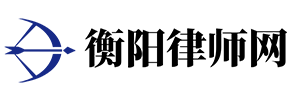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绑架罪的客观方面是单一行为,只要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并实际控制他人人身的,就构成本罪既遂。笔者以为,绑架罪的客观方面宜解释为复合行为,即由绑架和勒索或者提出其他不法要求等两个行为组成,其既遂应以实施了复合行为为限度,但不以勒索到他人财物等危害结果为标准。具体理由阐述如下:

第一,从刑法解释论角度看,在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罪状表述中,其字面含义确实仅仅突出了绑架”行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可以理解为构成本罪的主观要件。然而,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均告诉我们,对于法条含义的解读通常不能停留于字面,大多还需要进行论理解释,以使解释的结论具有系统合理性,符合刑法之实质合理主义的基础立场。那么,评价解释结论是否符合刑法基础立场的标准是什么?实现刑法实质合理主义的路径何在?
笔者认为,就解读个罪法条而言,首先有必要对具体犯罪的罪质与罪量进行准确、充分地评价。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犯罪均是罪质与罪量的有机统一体,罪质揭示某种危害行为侵害的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罪量标示该种危害行为对于一定法益的侵害程度。这种罪质、罪量关系在刑法解释论上的意义在于,具体犯罪不仅受到特定罪质的限定,还受到一定罪量的制约。如果超出了一定的罪量范围,罪质相同或相近的危害行为,也有可能成立他种犯罪。也就是说,罪量对于具体犯罪的罪质范围往往具有界定意义。于是,如何衡量、把握罪量就成为解释、认定个罪中的又一个关键性问题。绑架罪被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罪章,其主要犯罪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其次要客体是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利。据此,我们不妨把绑架罪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极重罪故意杀人罪作比较,如果把绑架罪罪状中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仅仅解释为主观要件,很显见,所剩下的单一的绑架人质行为就很难说比故意杀人行为的危害更大。况且在犯罪目的和动机方面,主观恶性更大的故意杀人罪也并不鲜见,而立法者并未因此匹配如同绑架罪一样严重的法定刑。换一视角透视,是否因为绑架罪在严重危害公民人身权利的同时还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利呢?答案似乎也不能仅止于此。因为抢劫罪同样是侵犯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之双重客体的严重犯罪,其法定刑还是相较为轻。至此,从合理解释罪状的角度说,笔者感到只有把绑架罪的客观方面解释为复合行为,这样才既可与抢劫罪相衡平,也可在犯罪系列中找到绑架罪之罪质、罪量的实在位置;即绑架罪一经实施(包含劫持人质与勒索他人两个行为),不仅严重侵害公民多人的人身权利(除严重危及被绑架者的人身安全外,还同时给被勒索者造成持续的巨大精神强制和压迫),而且严重威胁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利,这是单纯的故意杀人罪或者抢劫罪在社会危害性程度上都有所不及的,因而才能是绑架罪之罪质、罪量的适当归宿。
第二,从设定既遂标准的依据方面考察,各种犯罪的既遂形态有行为犯、结果犯或者危险犯等不同的种类之分。这里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不同犯罪的既遂形态分别归属于上述不同种类的依据是什么?理由何在?这对于正确界定绑架罪的既遂形态无疑是重要的。
依笔者所见,各种犯罪既遂形态的设定,主要取决于具体犯罪案发时的常见状态,也就是说,具体犯罪通常进行、持续到什么程度或状态下案发,这种常见状态一般就可确定为相应犯罪的既遂形态。具体说,如果案发时危害行为正在实行过程中,如运输毒品犯通常是在运输途中被抓获,则该种犯罪的既遂形态宜设定为行为犯。如果案发时危害行为已经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如故意杀人罪常常是以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为线索以案找人”而破案,则该种犯罪的既遂形态可认为是结果犯。如果案发时危害行为正在实行或者实行完毕,造成法益面临现实紧迫的危险性,如放射等危险性物质的投放者是在投放行为致使公共安全遭受现实紧迫的危险性时被抓获的,则该种犯罪的既遂形态应确定为危险犯。之所以将案发时具体犯罪的常见状态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依据或标准,主要理由在于:虽然犯罪既遂形态描述的是各种犯罪的最后停顿状态,但其并不完全以犯罪人意图实施的全部犯罪行为实行完毕或者达成犯罪目的为依归。那么,确立何种时间节点作为各种犯罪的最后停顿状态才为适宜?从立法者设立犯罪停止形态的初衷看,各种犯罪的法定刑应当是以犯罪既遂形态为标本而配置,因为对于预备犯、未遂犯或中止犯等未完成形态之罪的处罚,在法理上都是以既遂犯为参照,在事实上都是以法定刑为基础而进行适度修正与调整。由此可见,犯罪既遂是基本的、主要的犯罪停止形态,其他未完成形态均是修正的、补充的犯罪停止形态。换句话说,犯罪的完成与未完成形态在立法设计上已存在明确的主次关系,不可错位或颠倒,应当在具体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中得到凸显或体现。基于此,不难想像,如果把既遂的时间节点设置得晚于案发的常见形态,则势必导致实际追诉的具体犯罪大多呈现未完成形态,既遂形态沦为少数或例外情形。这种现象既与上述立法初衷相悖,客观上也很容易滋生刑罚适用上宽缓失度的弊端。相反,如果将既遂的时间节点设置得早于案发的常见形态,则意味着实际追诉的具体犯罪在案发前就已经既遂,未完成形态基本上就失去了产生的空间或余地。此种现象显然也不是立法的本意,客观上使刑罚适用缺少必要的弹性而显现僵化与严苛之弊。因此,以具体犯罪通常案发的时间为节点,以此时的常见状态为依据确定既遂形态,此标准既能契合上述犯罪完成与未完成形态的主次关系,实践上也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性。这里应予指出的是,笔者主张以具体犯罪案发时的常见状态为标准认定既遂形态,并非意指没有例外情形。事实上,举动犯作为犯罪既遂的类型之一,就往往发生和存在于案发之前。究其缘由,举动犯通常危害社会剧烈,立法上不能给其留有延伸的空间,将其既遂的时间节点大大提前,正是表明了法律上对其严厉的否定评价态度。质言之,将极少数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设定为着手就既遂”的举动犯,是刑事政策上的刻意为之,但不能作为绝大多数犯罪常规的既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