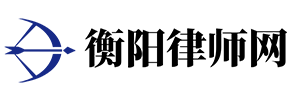2018年1月,在明拆迁律师梁红丽代理了一起村集体土地投资开发合同纠纷案件,合同双方为北京某旅游发展公司与北京某区某村委会,委托人为北京某旅游开发公司。

梁律师接受该旅游开发公司咨询的时候,公司已经作为被告被某村委会以违约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受理法院为北京市某区的基层法院。
梁红丽律师敏锐捕捉到了双方提交的合同文本内容存在的出入,通过提起管辖权异议将案件提至中级法院一审。
那么,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基本案情:见着收益要反悔?】
梁律师代理案件之后,经过与委托人的深入沟通,大致知悉了该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案情。
2001年,公司与村委会签订了一份村集体土地旅游开发合同,通过协议拆迁等形式取得了某村委会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后依法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投资国家鼓励发展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生态休闲旅游建设以及高端养老服务等综合性旅游开发项目。
自2001年签订合同至2018年提起民事诉讼,项目已经持续投资17年,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农业建设已经取得初步成果,项目已进入取得收益的阶段。
某村委会看到该项目收益后,想收回该项目自行开发,但是委托人显然不会同意村委会这样的无理要求。
就此,村委会以委托人违规开发、违反合同约定等事由,要求法院认定合同无效。
代理案件之后,通过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的梳理比对,梁律师发现,原告村委会提交的案件关键证据,即村委会提交的双方2001年签订的投资开发合同复印件与被告所持的合同原件不一致。
委托人所持的合同原件中的投资金额显示,投资总额为1.6亿元人民币,而原告村委会提交法院的合同复印件显示的合同金额只有8000万元人民币。
这一细节的差别让梁律师敏锐的认识到,受理案件的基层法院对本案可能不具有管辖权。
并且,经过多年的持续投资以及持续的建设,该项目的总资产实际金额已经远远超过2亿人民币,涉案金额重大。
同时,委托人经营投资项目期间,招用了大量搬迁的原住农民投入生态农业的建设项目,假使合同无效,委托人以及招用的大量工人也将受到重大影响。
【法律分析:管辖权异议成关键】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一)重大涉外案件;
(二)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很显然,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的法定情形。
就本案而言,合同金额巨大并且涉案人数众多,是否属于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呢?这就需要了解北京地区中级法院管辖的范围和依据。
根据现行有效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北京市三级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及高院执行案件的通知》(京高法发〔2011〕270号)第二条的规定,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
该投资合同纠纷案件,合同金额为1.6亿元人民币,并且涉案人数众多,依法属于北京某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该区基层法院没有管辖权。
进而,梁律师在答辩期限内,依法向该区法院提交了《管辖异议申请》,要求区法院将案件移送上级管辖人民法院审理。
很快,该区立案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将案件移送上级管辖人民法院受理。
为什么梁律师会对管辖法院如此敏感呢?这不仅仅是委托人涉案合同金额巨大的因素,更与我国两审终审制的司法制度有关。
两审终审制度,产生的司法现象是,绝大多数案件,集中在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即审理终结。
而基层法院审理一审案件,经常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简单的案件还好,即使有点偏差,当事人即使有损失,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是重大案件审判的偏差,当事人的损失就会十分巨大。
并且,中国的司法实际是,二审法院改判的几率很小,这样案件的一审对当事人而言至关重要。
同时,单就对法律以及证据的分析与认识上看,基层法院的法官与中级法院的法官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因为认识上的因素导致的司法判决的差异,也不在少数。
同时,基层法院的法官,也很容易受到基层熟人社会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的影响,人为将案件的管辖权控制在权力影响范围内的情形,进而控制案件的审判结果的情形也不在少数。
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或者异地管辖,也是受这个因素影响而建立的制度。
单就本案,在区法院的立案环节,对大额合同纠纷,法官就未认真、严格审核合同原件与合同复印件的差异而产生的管辖权问题,很难排除基层熟人社会人为因素对法官产生的影响。
管辖权异议,对当事人而言,仅仅是程序性上的权利,似乎不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实质的影响,但是,结合中国司法的实际情况而言,因管辖异议成功而导致的管辖权移送,对当事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本案而言,委托人案件管辖权的上移,可以有效避免基层法院熟人因素的不利影响,是对当事人意义重大的程序性救济举措。